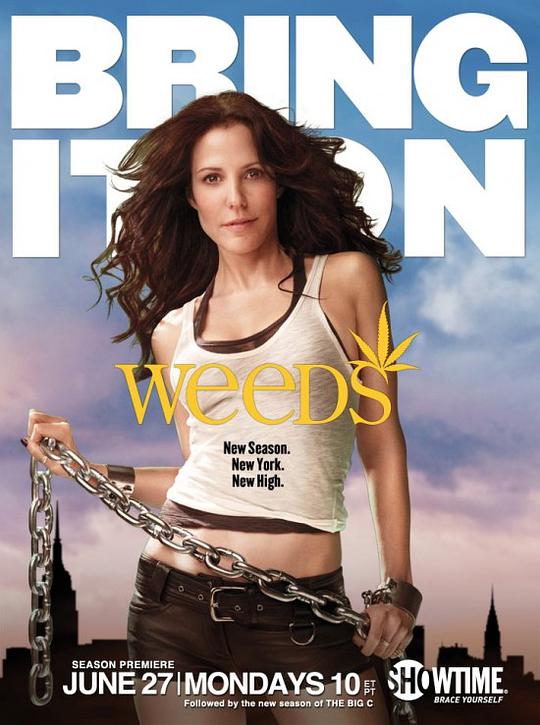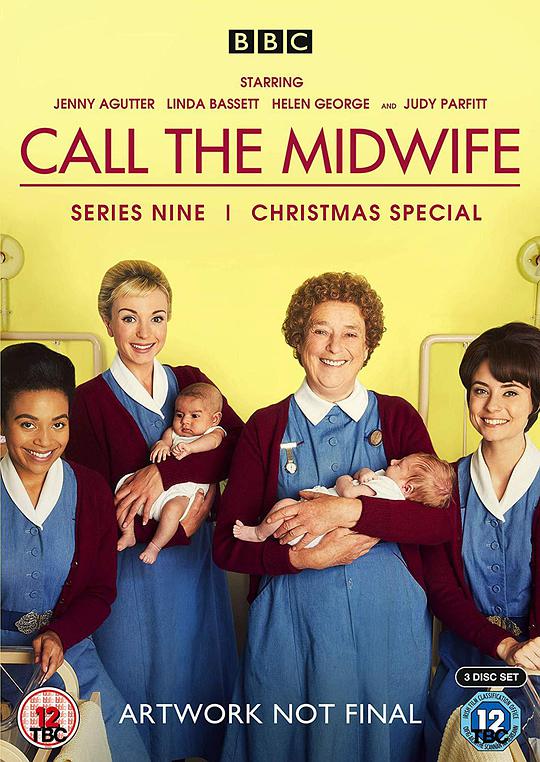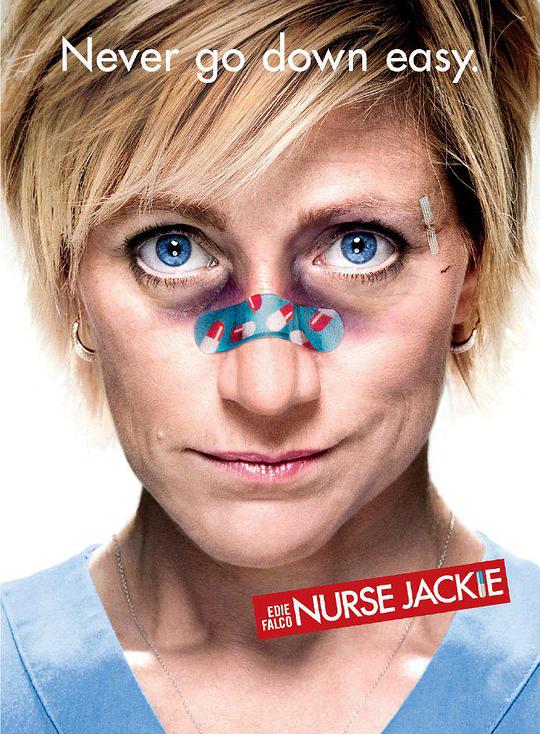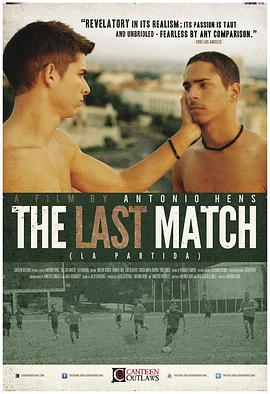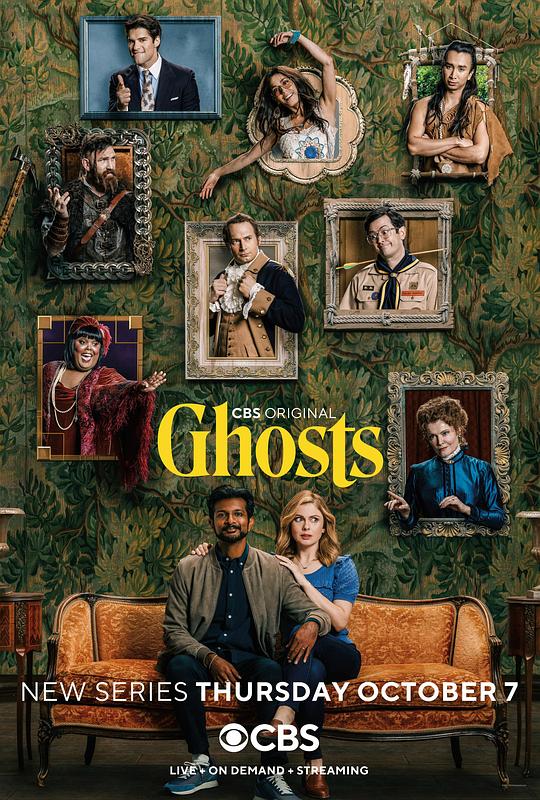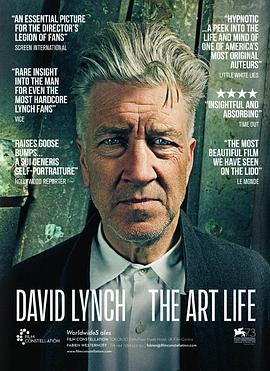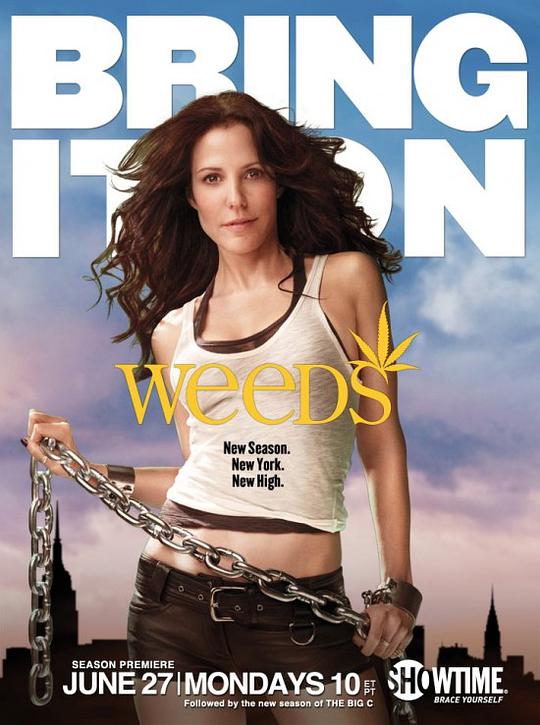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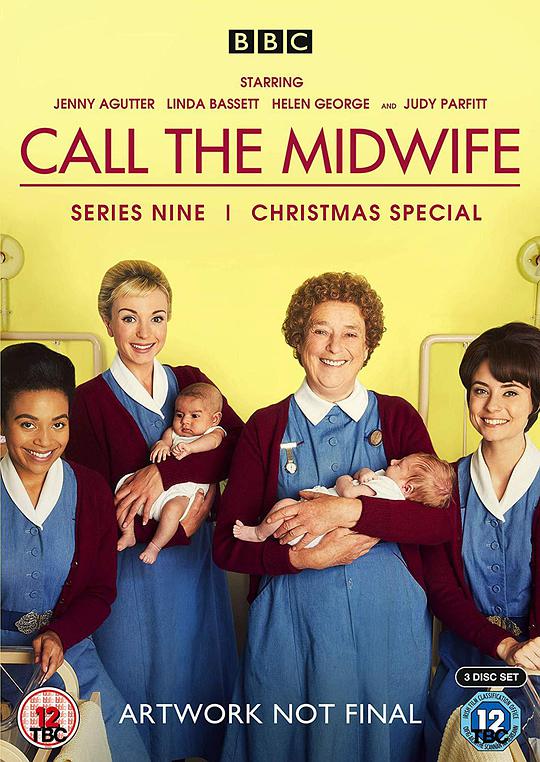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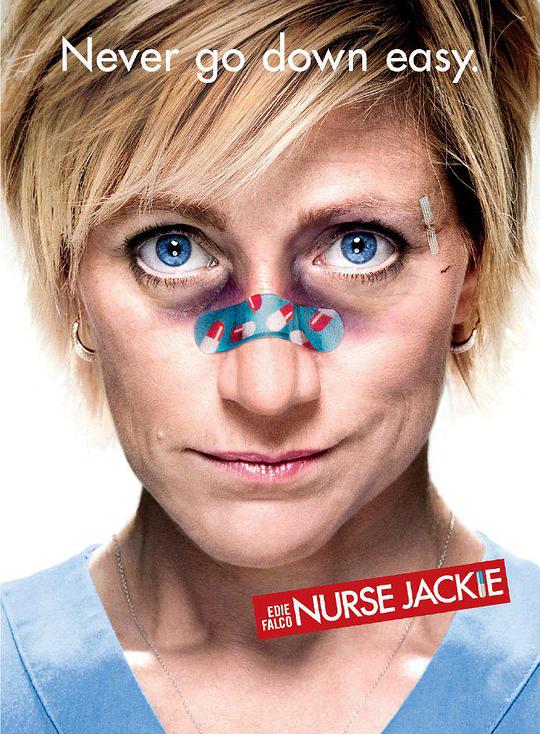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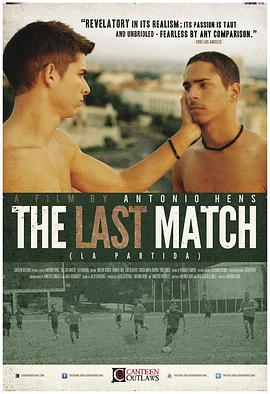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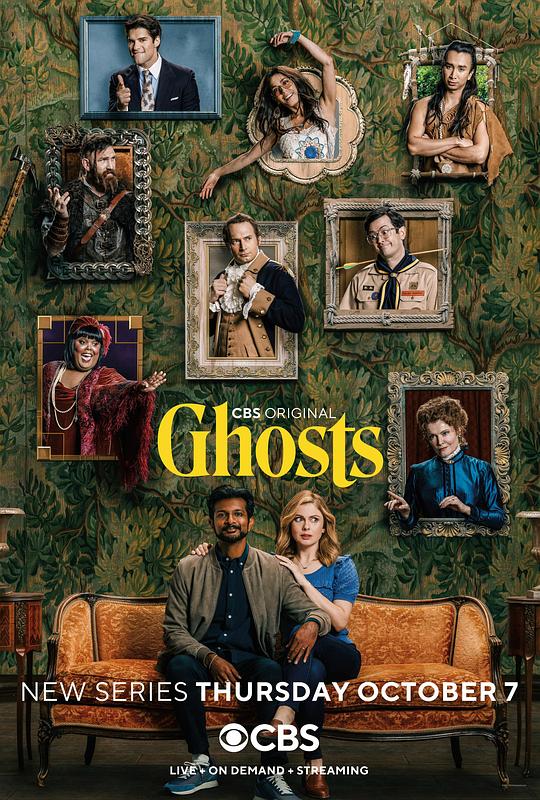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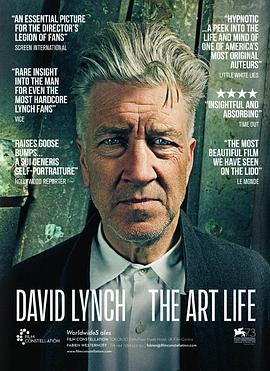






就在对于元清历史争论不休的时候(其实,本来没啥可争议的,是很多人掉入了日本人“满蒙非中国”的陷阱),看到了一条新闻。
12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等部门在上海公布2023—2025年取得的重大考古成果。其中一项聚焦红山文化,综合两年来辽宁、内蒙古、河北的红山文化考古成果,发现5000多年前,红山文化并未消失,而是向西向南拓展,并把相关礼仪体系融进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大脉络里。
我想到的是,如果按照那些个大汉族主义者的讲话,不承认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那么,有些人的祖先是哪里来的?石头里蹦出来的吗?
那些个骂元朝清朝的人,很有可能是在骂他自己的祖先,说不定他祖先就从红山文化走出来的。
那些在无意中附和某些外来解构话语的言论,是否可能在文化的意义上,演变成一场针对自身远古渊源的、充满反讽的“骂祖”行为?
红山文化,被视为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一颗遥远而略显神秘的北方星辰,以其精美的玉器(尤其是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C形玉龙)和宏大的祭祀遗存闻名。
此次公布的成果,赋予了它全新的动态意义。关键在于两个动词:“拓展”与“融进”。
“拓展”意味着能动性。约五千多年前,当红山文化在其核心区达到鼎盛后,并未封闭或衰亡,而是携其成熟的礼仪观念、社会组织能力和技术,主动向西南方向的燕山南北、乃至更远的中原文化区辐射影响力。这种拓展不是军事征服的号角,而是文明软实力的涟漪。
“融进”则标志着本质的升华。红山文化并非作为一个异质体被吞并,而是将其核心的文化基因——对天地祖先的崇高信仰、以玉器为载体的等级与礼仪观念、对龙这类神圣符号的塑造——贡献出来,参与到了更宏大的文明熔铸工程之中。
它的玉礼制,与同期或稍晚的中原玉文化交相辉映,共同奠定了后世中国“玉文化”的基石;它的龙形象,更是成为中华民族最具认同感的图腾符号,其血脉延续至今。
中华文明从其曙光初现的“古国”或“邦国”时代起,其发展逻辑就不是单一中心的直线膨胀,而是多区域、多系统在持续不断的互动、碰撞、借鉴与融合中,逐渐凝练出共同价值与认同的过程。
“多元”是鲜活的、各具特色的源头活水;“一体”则是百川归海、你中有我的历史结果与必然趋势。
红山文化,正是这多元中杰出的一元,并且是早期主动参与“一体”构建的关键成员。将中华文明简化为单一源头的叙事,在红山等考古发现面前,已不攻自破。
理解了红山文化所揭示的文明早期融合模式,我们便获得了一把钥匙,用以审视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族群关系与王朝性质,尤其是元、清两朝。
红山先民的后裔,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融入了其后在东北亚草原与森林地带兴起的诸多族群,如东胡、乌桓、鲜卑、契丹、蒙古、女真(满族)等。
这些族群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互动,构成了中国北方边疆史的主旋律,其方式无外乎贸易、移民、战争、和亲,以及——如红山文化所预示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吸收与政治整合。
元朝与清朝,正是这种数千年互动融合过程中,所产生的最具代表性、也是制度最为成熟的两个政治结晶。
元朝(1271-1368)由蒙古族建立。它固然有民族等级制度等时代局限性,但其历史贡献根本性地塑造了“中国”的形态:
疆域整合:它首次将青藏高原、云南高原完全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行政管理体系(宣政院、行省制),基本确立了近代以前中国疆域的极大轮廓。
制度创新:行省制度,成为后世中国地方行政区划的蓝本,极大地强化了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治理能力。
文化交汇:空前的东西方交流,以及元曲、科技等领域的成就,都是在多族群共存的背景下绽放的。
更重要的是,元朝统治者自忽必烈始,便以“中国之主”自居,定国号“大元”取义《易经》“大哉乾元”,承继中原王朝法统,采用汉式官僚制度与典章礼仪。
它不是一个外来的、纯粹的“蒙古帝国”在中国地区的临时统治,而是一个采用了多元治理模式的中国王朝。
清朝(1644-1912)由满族建立。其在“多元一体”的构建上走得更深更远:
疆域定型:通过一系列军事、外交与政治手段,最终奠定了现代中国领土的法理与事实基础,其版图被此后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基本承袭。
族群治理:形成了一套针对汉地、蒙古、西藏、回部等不同地区的差异化但高度有效的治理体系,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护了庞大帝国的统一与稳定。
文化继承与认同:清朝全盘接受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皇帝不仅是满族的族长,更是天下的共主,以儒家经典治国,尊孔崇儒,编纂《四库全书》。
至清末,朝廷与士大夫皆以“中国”自谓,孙中山“驱除鞑虏”的口号很快被“五族共和”的共识所取代,这本身即说明清朝已被历史内化为中国王朝序列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从红山文化的“融进”,到元清两朝的“纳入”与“统治”,历史逻辑一以贯之。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政治共同体,其边界和内涵是动态扩展的。
扩展的动力,正是周边族群及其文化不断被吸引、融合进这个以中原农耕文明为基干,但又不断吸收新元素的文明体系之中。
元与清,是这个扩展过程中体量最大、制度成熟、影响深远的两个阶段。否定元清的中国属性,就如同否定红山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一样,是在斩断自身文明成长的关键链条。
那么,为何“元清非中国论”及相关的狭隘民族主义叙事,仍有相当市场?其根源复杂,但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近代屈辱的错位归因:中国在近代遭受的深重危机与屈辱,始于晚清。一些简单化的历史叙事,容易将这种整体性的制度落后、技术代差所带来的失败,情绪化地归结为“异族统治”的“原罪”,仿佛换一个汉人王朝就能避免。这忽视了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和工业革命带来的颠覆性冲击这一更宏大的时代背景。
西方与日本学术政治的话语投射:“元清非中国论”并非中文互联网原生思想。其学术根源可追溯至部分西方“新清史”学者(强调清朝的“内亚性”而非“中国性”)以及战前日本为侵略东北(满洲)制造法理依据而鼓吹的“满蒙非中国论”。这些论调带有鲜明的解构中国历史连续性、为其地缘政治目的服务的色彩。国内一些论者,在不察其政治潜台词的情况下,将其作为“学术前沿”引入,客观上成为了这类话语的“二传手”。
身份焦虑与简化的历史共情:在社会快速转型期,部分人可能产生文化身份焦虑。一种强调“纯粹”、“正统”、“辉煌”的历史叙事(很多人将明朝绝对理想化),能够提供简单直接的情感慰藉和认同锚点。这种叙事需要树立一个对立面,而被贴上“异族”、“落后”标签的元清,便成了完美的批判靶子。它满足了非黑即白的认知习惯和情绪宣泄的需求。
对“民族”与“王朝”概念的机械理解:将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国家”模型,生硬地套用于前现代的中国。在古代中国,王朝的合法性基础是“天下”观与“天命”论,文化认同(“夷夏之辨”的核心是文化而非血统)远比纯粹的族裔身份重要。用民族主义尺度去衡量古代王朝性质,是典型的时代错置。
从分子人类学角度看,现代中华民族,尤其是北方人群,是一个数千年来多次族群融合的复杂产物。
一个今天持有“皇汉”观点的人,其基因谱系中,极大概率包含了来自北方草原、东北森林地带的古代族群成分,而这些族群正是红山文化后裔融入的脉络,也可能是蒙古族、满族先民的渊源之一。在血统上,他可能正是他所斥为“外虏”的元清统治族群远亲的后代。
从文化传承角度看,那些人所珍视并认为被元清“破坏”或“中断”的“华夏文明”,其核心要素(如龙图腾、玉文化、礼仪观念、大一统理想)本身就是一个融合体。他们引以为傲的,很可能就包含着红山文化的馈赠,以及元清两朝在制度、疆域、文化整合上加固了的文明框架。
因此,这种极端排他的历史叙事,在考古学与遗传学揭示的漫长融合史面前,陷入了一种无奈的自我解构——
它在试图净化历史的同时,可能正在否定自身存在的部分历史根基;它在激烈排斥“他者”时,或许正将部分“自我”驱逐出门。
红山文化的最新考古成果,其现实意义远超学术范畴。它为我们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无比深厚的历史底气与实证支撑。
共同体不是近代以来被建构的“想象”,而是有几千年根基的“历史事实”。中华大地上的各族群及其先民,自文明初曙便开始了一场浩大而持久的“交往交流交融”。
冲突与竞争是插曲,融合与发展才是主旋律。
红山文化汇入中原,元清王朝统合四方,都是这部宏大史诗中的关键章节。
像红山考古这样扎实的科学研究,揭示出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生动而具体的历史过程。
让石头说话,让遗存作证,让跨越数千年的文明融合轨迹,自然而然地涤清那些被政治话语或情绪偏见所蒙蔽的认知。
五千年前,红山先民携其礼仪文明,向西向南,融入了中华文明初升的曙光。
今天,这缕穿越时空的曙光,应当照亮我们所有人的心扉,让我们能够坦然拥抱自身复杂而辉煌的融合血脉,在理解历史的深厚中,真正树立起不可动摇的文化自信与共同体认同。
否定元清,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在否定像红山文化那样,塑造了我们所有人的、波澜壮阔的融合故事本身。